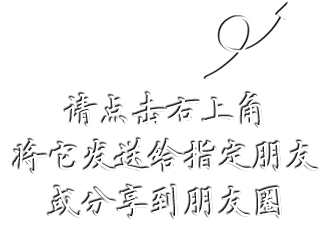-
价格:¥99999.00/件
-
起订:5件
-
供应:10000件
北京京城记忆——胡同儿里的大酒缸
酒是在柜台的酒坛里打。打酒用提子,是用竹筒截断旁边留一柱形提梁刮削而成,用筒内容积度量,有一斤、半斤、二两、一两四种。打酒时提子的速度很快,有“紧打酒,慢打油”之说,这是因为油的黏度大,慢打则将附着提壁的油滴回原处,酒容易挥发,敞口时间越短损失越少。盛酒的家伙什是叫酒嘟噜的又细又高圆锥型瓶,上口很小,装二两酒。如果您想喝热的,就把这个酒嘟噜泡在热水里片刻。酒盅大多是二钱的小茶碗。便于一口干。
大酒缸开设的地点是在胡同里,来这儿喝酒的绝大多数是街坊四邻,所以,这里洋溢着独有的胡同亲情。特别是冬天,一个大汽油桶改制的煤球炉子烧得旺旺的,炉台上两只大铁壶永远冒着热气,一进门就暖哄哄的。二两酒一盘花生米,几个老爷子一凑合天文地理大事小情神侃一通,得便就把娶儿媳妇嫁闺女老两口打呕气家里的烦心事儿议论议论开导开导顺顺气。通常说“借酒浇愁”,在这里可以说是二两解烦。如果您饿了,又不想回家,就让掌柜的小儿子到饭铺叫半斤炒饼,路过赶马车的喝酒歇脚需要垫补时,刚拿出冻得棒硬的窝头,掌柜的立马递给铁丝编得烤架,让烤热了再吃。有时老街坊路过喝二两,虽然贴着“小本经营,概不赊欠”的告白,只要说句“先挂着”,掌柜的往水牌子上大笔一挥,您就走您的,什么时候结账,擦去就是。
蒸酒缸缸好 做醋坛坛酸
妈妈干地里的农活一直是把好手,印象中各类人吃的、猪吃的菜蔬,从不缺什么。但妈妈在农产品加工这方面,比外婆差很多。比如辣酱、豆豉、萝卜头等。妈妈则一直不太承认,说是外婆家的坛子好一些。
做酸菜的坛子好的是那种会呼吸的。因为外檐是放了水的,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角落里的酸坛子会冷不丁的发出一种极像放了一个响屁的声音,让你忍俊不禁。
外婆做得好的是辣酱辣子。熟悉永丰辣酱的人都知道,辣酱在缸钵里时好吃,但凡入了坛子,就掉了味。但藏在坛子底下的鲜红辣椒,可谓是吸取了辣椒的灵气,既秀色可餐,又美味爽口。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入了坛子的辣酱就如女子下了嫁,而辣酱辣子,就是女子孕育的新生命。
外婆会选那种肉体厚实,够长、够靓的红辣椒,刷洗干净,晾干,用剪刀从前端入手,剪一条斜缝,在辣酱装坛子以前,置于坛底,再把晒好的辣酱装进去,密封好。静置十天半个月,辣子就可以夹出来吃了。只是用筷子往坛子底下捞辣椒时,有点费劲,两只手还总会沾些辣酱。
辣酱辣子辣中带甜,是很好的下饭菜,完全不逊色于霉豆腐腌出来的姜丝或萝卜条。食量一直不大的我,就有用一个辣椒吃完三碗饭的经历。只是妈妈和外婆早就离开了我,我也很少再能吃到地道的辣酱辣子了。
民国学界的酒缸、酒鬼与酒仙
“酒缸”章太炎先生
与老师相比,黄侃则是标准“酒鬼”一枚。这位“疯子教授”对于杯中之物的贪嗜,绝非一般人所能想象也。黄侃每餐都要豪饮,至少入肚半斤。且黄对酒从不挑剔,汾酒、、杏花村,他来者不拒;糟醴、生啤、白兰地、伏尔加,他也一一笑纳。喝到酩大醉、东倒西歪、吐出胆汁、枕眠路边,实在是稀松平常之事。而这位“酒缸”黄侃居然还劝别人喝酒要节制。据其日记载,有一次至交林公铎“自温州至,下火车时以过醉坠于地,伤胸,状至狼跋”,黄认为“似此纵酒,宜讽谏者也”。酒鬼劝醉鬼,莫贪两三杯,读至此处,笔者忍俊不禁,险些因其晕倒,真乃怪事哉!也正拜酒精刺激,黄氏撰文往往一气呵成,酣畅淋漓。
-
公司:重庆昆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
姓名:丁小龙(先生)
-
电话:18458196875
-
手机:18458196875
-
地区:重庆
-
地址:重庆重庆市重庆主城区覆盖
-
QQ:346655709
-
0人关注0人点赞举报